我身边的亲情故事——曾氏父子
劳 罕
清明节前,新闻圈有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条信息:“老曾去世三年了,怎么从没见你给他写点什么?他朋友不多,你可是他经常念叨的一个哟!”
其实,早就想写写曾老师,可一直不知道该怎样下笔。写那种无话找话、歌功颂德的谀文,凭我对曾老师的了解,他肯定不答应。说不定嘴一撇,又是满脸的不屑:“瞧,你小子也堕落了!”
可真要写那个真实的曾老师,却又不忍心:不单是为逝者讳,更主要的是,有的事说出来真的很残忍。
思考再三,还是写了。职业的底线要求我不加矫饰,既写写他的长,也揭揭他的短。我相信,泉下有知,曾老师是不会怪罪我的。
这不嘛,晚年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过错。尤其是在对待爱人、儿子这件事上,他竭尽全能补过。
一
大四上学期,按照学校教学安排,我到京城一家报社实习。实习期三个月。因为班主任和这家报社的老总是大学同班同学,事先他曾修书给老总。所以,我得以直接面谒老总。
记得报到那天,那个很儒雅的总编辑把眼镜往鼻梁上方推了推,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:“你们班主任的信,我收到了。他说你的文笔不错,喜欢研究问题。那就到工商部跟着老曾吧。这个人脾气有点臭,但论业务水平,全报社比他强的还不多,可以称得上是专家型记者。平素,对稿子要求也非常严格。初学步,你跟着他,有好处。”
尽管老总打了预防针,第一次见曾老师,还是被他的“臭脾气”惊得够呛。
那天,老总的秘书带我去和曾老师对接。这是一个身量不高、已经有些发福的中年人。他的皮带勒得很靠下,如此便显得腹部硕大、很夸张地向前凸着;他的面色黧黑,脸颊的肉有些松弛、下垂;眉毛很浓很重,一说话,额头就像有两条横卧的黑蚕在蠕动。
说实话,以后来我对他的了解,他的相貌远远辜负了他的才学。
秘书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,末了,加重语气说:“这是总编辑亲自安排的!”
谁知曾老师并不买账,眉头一拧,那两条黑蚕便挤成了一个疙瘩:“又给我塞实习生!我带得过来吗?”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,“没见我忙成什么样子了!刘秘书,回去告诉头儿,误人子弟,可不是我老曾的风格。别人可以那样做,我老曾,不能!”
秘书很尴尬,朝我扮了个鬼脸,悻悻地退了出去。
曾老师也不搭理我,自顾自狠命地一口一口抽烟。他面前一个硕大的陶瓷杯里,烟屁股早都溢了出来。
我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——也根本不知道该坐在哪里。
他过足了烟瘾,把烟屁股往杯子里使劲一摁,这才侧转身指了指角落里的那张桌子:“坐那里!”说完,又不理我了,埋头看起报纸来。
我闷坐了一会儿,怯生生问道:“曾老师,接……接下来,我……我该干……干什么……”
“该干什么?你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?拉屎撒尿都要问老师?”
说完,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了点,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我,一字一顿地说:“先-看-报-纸。你看我不是在看报纸吗?想学本事,就得有眼色。”稍顿了一下,才接着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让你看报纸吗?入乡问俗,你先要了解本报的特点。即使老记者,看报也是基本功,通过看报知晓时政大势和当前的报道重点。”
这第一课,对我此后的从业大有帮助。这么多年来,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,许多的新闻敏感、新闻线索、新闻策划就是从触类旁通中发掘出的。
二
这间办公室,一共坐了6个人:除了曾老师,还有三位记者。此外,我那张桌子对面还坐了个女孩,也是个实习生。
女孩姓方,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,也由曾老师带。不过,她马上实习就要结束了。
小方是北京人,很时尚,也很乖巧,待人很热情,时不时会带些零食放在每个人的案头,包括我这个实习生。办公室其他三位老师都很喜欢她。
可曾老师对她颇有看法。每天上班时小方和他打招呼,他都置若罔闻,带搭不理地鼻孔里哼一声。
一次,小方用门背后挂着的一条旧毛巾揩了揩桌面,被曾老师察觉了。明明知道是小方干的,他完全可以当面告诉她:这是我擦脸的毛巾,今后不能这样了。可他没有那么做,而是找来一支毛笔在一张版样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:“这不是抹布!”然后贴在了毛巾旁边。
还有一次,不知小方又误了什么事,曾老师铁青着脸狠尅了她一顿。下班了,曾老师还在生闷气。见他未走,我只好留下来陪他。
他一根接一根抽了五六支烟才余怒未息对我说:“你看她那个样儿,是来学习的吗?给她讲怎样改稿,她眼神飘忽、神游八荒,能听进去才怪呢!采访也是一样,不专注听采访对象讲,眉眼飞来飞去!哎呀呀,我真不想带她……你小子,可不能学她!”
对于实习,小方有自己的见解。有一次,办公室只有我俩时,她告诉我:“毕业后,打算出国。再说了,这蜻蜓点水的两三个月实习能学到什么?说白了,就是借实习这个机会多走走看看,游山玩水呗。嗨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!”说完,又神秘地低声说:“曾老师这个人,各色,报社没有几个人喜欢他。你知道吗?他经常对老婆家暴。和自己的儿子也死掐呢!”
三
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曾老师,就业务而论,他的确有两把刷子。
他喜欢写述评。他的述评,逻辑缜密、思想深邃,总有独到见解。更让我惊叹的是他的文采。
一般而论,以深度见长的文章,多不注意文采。新闻圈在鄙薄一个记者的时候,往往在说了他的一通不是后,末了来上这么一句:“这个人,文采还行。”
曾老师的文字,极其干净。曾有一个老编辑这样评价他:“遇到版面需要删活儿,老曾的稿子,只能由他自己删。别人删,哪怕删个字,就接不上气了。”
搞文字的都知道,文字真能做到干净,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那是需要披沙拣金、千锤百炼的!
不独干净,曾老师的行文还很是优美:用词考究,简约的文言文被他很“白话”地活用,历代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嵌入文中,通篇读来,满满的书卷气、清雅气。
我起初的几篇稿子,被他修改后,属于自己的,恐怕就是几个标点符号了。我惭愧得直冒冷汗。
一次,我惴惴不安问曾老师怎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。他很得意:“小子,难啊!别说你一个实习生,报社乃至整个新闻圈,有几个人敢和我比?”
见我一脸沮丧,他宽慰我:“最近,听你们年轻人经常哼这样一句歌词,‘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,没有谁会随随便便成功。’流行歌,那是垃圾。可这句写得不错!小子,要想人前显贵,必须人后受罪。告诉你一个写好文字的秘诀——大量地背诵。有人反对死记硬背,那才是误人子弟。只有背会的,才是你自己的。我从小就喜欢背诵,语文书能从头背到尾;老三篇、毛主席诗词也都倒背如流。大学毕业后,在农场改造那些年,又把古文观止、史记、资治通鉴背得滚瓜烂熟。至于汉赋晋文唐诗宋词,随你挑吧,看看哪篇我不会?”
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《经济述评钩探》,在扉页上龙飞凤舞写下这样几行字:“论写述评,我老曾在新闻圈说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!小子,好好学吧!”
这本书,我一直带在身边,一直在学。越学越气馁,越学越惭愧: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识、这样的思辨、这样的角度、这样的文采?说实在的,这辈子,我恐怕都达不到他的境界。
一定是一肚子诗书的缘故吧,他的口才也一级棒,妙语连珠,诙谐辛辣。和人辩论时,直奔要害,犀利刻薄,句句见肉。对方哪怕再有理,也会被他驳得哑口无言。
辩论时,他的肢体动作也很有特点:身体向左微倾,扬起的左手小拇指、无名指蜷缩,而其他三根手指半伸半曲,弧度很优雅。简直帅呆了!
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,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为革命事业辩护时,就是这样的动作。
工商部每周一下午都要开例会,除了传达上级精神、报道指令,再就是点评上一周的报纸。每逢这个环节,几乎就成了曾老师的专场。他一篇篇评点过去,把别人的文章批得体无完肤。可没有一个人敢挑他的丁点毛病。大家都躲着他。
话又说回来,他对文字精益求精,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来。
一次,一位姓杨的记者对他文章中的一个用词提出了商榷意见。曾老师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小时,对方囧得面红耳赤。他觉得还不过瘾,结语时说:“老弟呀,你恐怕还得把初中的语文先补一补。”对方恨不得地下裂道缝钻进去。
那天例会结束后,他心情大爽,拉我聊起了天: “哼,还跟我辩?姥姥!”
他不无得意地说起了年轻时候的事:大学期间,赶上了那个“特殊年代”,他是他们那个“战斗队”的司令。京城无论哪个“战斗队”和他们辩论,最后无不丢盔卸甲。
四
曾老师这个人,貌似脾气火暴、甚至有些古怪,其实,他心底也藏着柔情。
一次,他原定到合肥出差,临行前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。
他让我到北京站把车票退了。
那是一张硬卧票。那年头,买张卧铺票非常难。我一到退票窗口,马上有个人走了过来:“你要退票吗?如果是卧铺的话给我。省得你排队。”
我图省事,便原价给了他。
谁知当我兴冲冲地把票款递给曾老师后,他狐疑地看着我:“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?车票退给谁了?”
我说了经过。
“现在卧铺票很难买的。退给‘黄牛’的话,一般都会给个十块、二十块……”
我一下子明白了:他是认为我把回扣贪了。
我很委屈,转身到车站去找那个票贩子。
人倒是找着了,可人家死活不承认从我手里买了票。
怎么办?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呗!
我凑了20元钱,给曾老师送去:“我找了‘黄牛’,他给了20元……”
没承想曾老师一下子拉下了脸:“你给我说实话,是不是你自己垫的。我最讨厌别人骗我。”
“这事我没办好……”
“混账小子!你这是打我的脸。我这样给你说,是让你多长点社会常识。”
“我的责任,就应该我负。”
“还犟?那么,是不是我还得给你跑腿的小费?你这个浑小子!”
钱,他死活不要。
那天下班,他对我出奇地客气:“走,咱爷儿俩下馆子去!”
他请我来到王府井一家知名的馆子,点了烤鸭,还要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。结账时,我留意到,他付了67元。在当时,那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。
我俩边吃边聊。他讲起了自己的过往:
抗战胜利那年,他出生在鄂西北的一座小城。父亲是个小业主,母亲不识字,可父母对他的教育看得很重,把他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。从小,他便显露出了过人的天赋,记忆力超群,代数几何老师一点就通。考大学时,他以小城第一的成绩考入京城一所名校。他的志向是,毕业后当个外交官。
可那场史无前例的“运动”,阻断了他的前程。
由于年轻冲动,他成了“运动”的活跃分子。其间,还被结合进了专案组。那个参加过延安整风的校领导,被列为学校的头号“走资派”,每天都要向他这个“革命小将”请示汇报。
可就是因为这段经历,恢复高考后,第一年报考研究生,尽管他考分很高,却没有被录取。第二年接着考,考分全校第一,依然没有被录取。
他通过关系打探方知,当年那个头号“走资派”早已复出,并分管这所学校,偶然间察看考生名单时发现了他,便告诉校方:“这个人,参加过当年整我的‘专案组’。”
这么一说,校方哪里还敢录取他。
获悉这一情况后,他试着给这个领导写了封信,真诚忏悔。人家领导也很大度,很快便给他回了封信,勉励他接着考。这一次,他轻松过关。
说到这里,他不无懊恼:“当年真是吃撑了!后来活该在农场改造了几年。”他还讲了在农场的种种艰辛。
这时,我问了一句:“师母是不是也是在农场认识的?”
他似乎突然遭到电击一般,表情僵滞了,话也没了,埋头闷闷地吃起来。吃了几口,突然一拍筷子:“走吧!不吃了。”
五
那天那一幕,加上此前小方说的那番话,我判断,曾老师和爱人一定有着很深很深的矛盾。
可究竟是因为什么?我不敢打问。此后在和曾老师的交往中,也尽可能回避他的家庭问题。
不过,该知道的迟早还是要知道的。
曾老师的业务之所以出类拔萃,甚至一骑绝尘,与他的敬业大有关系。他采访时,不像有的记者,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写。他善于揪住蛛丝马迹、打破砂锅问到底,而且,采用求异思维,反向推导、多方印证。任何一个采访对象想搪塞他,万万做不到。那些所谓的“水货”行家、权威们,被他几个问题问下来,往往满头大汗。
他告诉我:“一个称职的记者,应该比采访对象更高明。采访对象未必知,你未必不知。因为职业特点决定了你不仅要读万卷书,而且要行万里路。其他行业的人能有这样的条件吗?不可能有。如果你不能站得比人家高,说明你的书还没有读够,或是你的路还没有行够。一句话,你还不称职!”
他不但采访扎实,写稿也极其认真。一遍一遍改,一遍一遍念,力求写出韵律感。他说:“文理通顺,那是中学生就该做到的事。像我们这种职业记者,篇篇都该是美文。”
他的这些理念,我至今都奉作圭臬。
他的心思,几乎全用在工作上了。那个时候,每周只休息一天。礼拜天,他经常让我到他西三环边上的家里改稿。我知道,他是想让我改善一下生活。
此前,他曾问过我:“礼拜天报社食堂停了,你们这些外地学生怎么吃饭?”
“只能瞎凑合呗。”我苦笑着如实相告。
第一次见到曾老师的爱人,是在他的家里。
说实在的,我怎么都不会想到,凭曾老师这副长相,竟能娶到这么一位漂亮的夫人。
一定是曾老师告知了家里要来客人的消息,我一按门铃,房门就开了:一位身材高挑、皮肤白皙的四十岁出头的女子迎在门口。
和她目光一遇,我便马上垂下了眼睑,因为她太漂亮了,惊得我不敢直视。
她有一双大大的丹凤眼,一头乌云般的大波浪长发。因为是在家里的缘故,她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淡青色的羊毛衫,下身是一条咖啡色的宽松休闲裤。
一看就知道,女主人的衣着极有品位。
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男孩,十四五岁的样子,大高个——比曾老师至少要高出半头。男孩长得非常俊朗,高高的鼻梁,大大的眼睛,卷曲的乌发,面部轮廓很像欧洲人。
男孩穿着也很考究:白衬衫扎在淡蓝色的西裤里,衬衫和裤子熨得笔挺,脚上是一双咖色的休闲皮鞋。
我愣怔了片刻,慌慌张张要换鞋,夫人拦住了我,笑吟吟说:“不用换。不用换。”然后,吩咐男孩:“林林,快叫叔叔!”
男孩甜甜地叫了一声:“叔叔好!”
我赶紧说:“叫哥哥就好。我是曾老师的学生。”
夫人说:“那怎么行。林林,记住,必须叫叔叔。”
“就叫哥哥!”打我进门开始,曾老师就一直坐着没动,不冷不热地看着母子俩。这时,他才接了话。
曾老师声量不高,但屋里马上沉寂了。母子俩明显变得惴惴不安,再无言语。
吃饭时,饭菜早端上来了,可母子俩依然待在厨房里。曾老师让我动筷。我说:“等等刘老师吧?”
事先我知道,曾老师的夫人姓刘,在一家剧场搞舞美设计。
“吃你的!”曾老师黑着脸。
“你儿子真帅!”我无话找话说。
他突然暴怒了:“你他妈的能不能不说他!”
因为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,我也不敢再言语,只能埋头扒饭。
以后,曾老师又请了我几次。每次都是我和他在客厅里吃,他夫人和儿子在厨房里吃。
一个礼拜天,曾老师临时有事,让我先到他家里去。
刘老师正在阳台上压腿,一看那身姿,就是专业出身的。
曾老师不在,家里的气氛便很活跃。刘老师告诉我,她小时候学过芭蕾舞,她父亲的愿望是等她长大后送她到苏联的瓦岗诺娃芭蕾舞学院留学。可后来,情况变了……
“别再做你的黄粱大梦了!永远改变不了你剥削阶级的本质!”因为厨房比较密闭,我们没发觉曾老师已回来了。
刘老师马上噤声,脸都吓白了。帮曾老师挂外套时,哆哆嗦嗦竟将衣服掉在了地上。
又有一次到他家,我到厨房帮着端菜时,林林悄悄对我说:“哥哥,听说你会武术。能不能教教我?”
那个时候,电影《少林寺》的余温还没有散去,但凡是男孩,都做着武侠梦。
“不允许!”客厅里的老曾耳朵很灵,威严地说。
饭菜齐了,动筷的时候,曾老师又疾言厉色地对我说:“你给我记住,不允许教他。如果偷着教他,你就给我滚出工商部。”
也可能是为了维护我,林林从厨房走了出来,委屈地说:“爸爸,为什么?为什么?”
“为什么?你还敢问为什么?你想挨揍!”
刘老师赶紧走了过来,把林林拉进了厨房。我发现,母子俩眼睛都泪汪汪的。
人与人之间,我始终相信缘分。打第一眼起,我就非常喜欢林林这个小弟弟。那张俊朗的脸上,带着热情、善良,可他的眼神里,又透着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该有的忧郁。
每次,我到厨房帮着端菜,他的目光始终热切地追随着我,想帮我,可刚一跨出厨房,又总怯怯地站定了。
有一次,我从他家里吃完饭出来,没走多远,他追了上来,塞给我一个纸包:“哥,我看你很喜欢吃这种饼。”说完,不等我推辞,一转身跑了。
这是刘老师做的一种小圆饼,麦粉和米粉混合而成,巴掌大小,薄薄的软软的,入口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。我曾在饭桌上夸过这种饼好吃。
办公楼的后面,是一条悠长的胡同。我住的招待所就在这个胡同里。一天下午下班,我刚走进胡同,林林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,热切地叫了一声:“哥。”我问他为啥这么晚了还不回家?他说,就是想来看看你。
我俩到附近的后海边转了很久很久。这时候的他,不见了怯生生的样子,很活泼、很健谈。我发现他读了很多很多课外书。
此后,他又来过好几次。
我明白他的小心思:很想学武术。但碍于父亲有言在先,他不敢明着提出。而我,也同样碍于这个原因,不敢主动教他。
其实,这是个很有家教很乖的孩子啊!
六
那次在曾老师家挨呲儿之后,我非常难堪,对曾老师也产生了一些情绪。所以,有一段时间,我刻意躲着他。他再请我去他家,我借故溜号。
他肯定是察觉到了,一天下班后,他没有去赶班车,让我陪他到后海散散步。
起初,他一言不发只顾往前走。从他一支接一支抽烟看,心里一定是波涛汹涌。
终于,他放缓了脚步。等我和他走齐了,突然说:“你也是个大小伙子了,你该知道什么是男人最该维护的尊严吧?”
我不明就里地看着他。
他叹了口气:“夺妻之恨,放在谁身上都不能忍!”
然后,给我讲起了他和刘老师的恩恩怨怨:
刘老师比他小一岁,和他在同一座城市长大。不过,刘老师的父亲是城里最大的资本家,在汉口也有很多买卖,有刘半城之称。
公私合营前,刘家有洋房、小车、仆人。公私合营后,就渐渐落魄了。尤其是“文革”袭来,刘父沦为人人唾弃的“五类分子”。
刘老师从省城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后,被发配到了一家军垦农场。这时,已是“文革”后期了,曾经很活跃的曾老师也因失势来到这家农场接受改造。
都是大学生,又同病相怜,很快两人便相爱了。可是不久,曾老师有了心病:农场“军管会”的头头经常找他爱人谈心,并且一谈就是很晚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被安排到农场最远的一个分场修大渠,而刘老师则被吸收到农场的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当报幕员。
有一天晚上,他临时从工地回来,见那位头头正从他的家里匆匆离开。这时,已快12点了。
“这么晚了,他来干什么?”他追问妻子。
刘老师说:“明天有最高指示发布,他来通知宣传队临时加演一场节目。”
曾老师问来问去,妻子就是不承认有私。那一晚,他第一次打了妻子两耳光。
一年之后,有了儿子。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,他就越来越生气:儿子,压根儿不像他。
“这样的事,换你,能忍吗?”曾老师左右手交替不停地揪着头发,有点歇斯底里了。
“可是,您有实据吗?”我问。
他愣了一下:“那晚,看到的,不是实据吗?那个狗日的,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,能干吗?”
“那个年头,连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,贯彻领袖精神不过夜。有了最高指示,要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。”
他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,问:“那么,儿子不像我,又是怎么回事?”
“可能更多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吧!民间不是这么说嘛,‘儿子像娘’。我看他和刘老师长得很像。影响遗传的因素很复杂,有的还是隔代遗传。您比我学问大,这点,您一定能想明白。”
他不吭声了。
我接着说:“说一句不该说的话,您这是疑心生暗鬼。我看人家刘老师,正派得很。再说,她那种家庭出身,在那种环境下,哪怕真有什么,也是被迫无奈的。您应该原……原谅她……”
“什么?原谅?你他妈的浑蛋啊!”他一把揪住了我的脖领子,头上青筋暴绽。
过了一会儿,也许觉得自己失态了,连声对我说:“对不起!对不起!唉——”
那一声长叹又粗又长,里面夹杂着悲愤、无奈和屈辱……
七
那次湖边畅谈,实际上并没有解开曾老师的心结。他依旧终日闷闷不乐,依旧不停地发着脾气。
看他这样,一天办公室就剩我俩时,我试着问他:“曾老师,这种情况,你为啥不和她离了?你俩这样耗着,多累啊!”
他显然有些吃惊,抬头死劲盯着我:“你说什么?离了?”眼神里满满都是愤怒。
他夹着烟卷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:“说得好听!离了?那我便宜谁?她的长相、气质,很符合我的审美……”
“很”字咬得很重。
在房间里足足走了几十圈,他才一屁股坐回了椅子,狠狠剜了我一眼,意思是你怎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。
后来,我在复盘曾老师、刘老师这段姻缘——这是时代造成的一场孽缘:如果处在升平世,两个都有着很好学养、情趣的人,一定会琴瑟和鸣、举案齐眉。但是,世事颠倒了,美丑扭曲了,一切便都移形错位,原该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。其实,从骨子里,曾老师一直深深爱着刘老师。因为深爱,他希望他们的姻缘里不夹杂丁点的杂质,容不得半点亵渎,是完完整整的。可是时代,凭空带来了许许多多个人无法抵御的杂质。杂质,让爱生恨。爱之越深,便恨之越烈。看到气质若兰的妻子、看到不像自己的儿子,越看就越有气。天天看,就天天生气,于是,就天天拿娘儿俩出气。
他这样,刘老师能回馈给他爱吗?肯定不能!一辈子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,实在是太残忍了!
其实,曾老师心里,时时刻刻都在呼唤着爱。一天,他在看一本杂志,突然放下杂志,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,压低声音说:“杂志上说,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浪漫,激情来了,在校园里大庭广众就敢接吻?真是这样吗?”
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。
“有没有?”不等我回答,他突然叹了口气:“唉!我家那个,从结婚到现在,从来就没有主动过。就像个僵尸……我这一辈子啊!”
八
毕业后,我分配到了京城的另一家报社。因为有这份师生之谊,我和曾老师来往比较密切。
总体看,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遂:因为性格的缘故,尽管每位总编都承认他能力超群,可始终没有重用他。退休前,他好像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。工商部他带过的学生都当了他的领导。
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。和爱人、儿子的关系也更加糟糕。
一次,朋友圈里流传这样一个消息,说曾老师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派出所。
原因是,随着儿子年龄的增大,性格越来越叛逆。到后来,根本不服曾老师的管教。譬如,曾老师让儿子晚上十点钟必须回家,可儿子故意过了十点钟再回来。两个人的矛盾便一天天升级,从口角变成了厮打。此时的曾老师已不是儿子的对手。
那天,儿子故意十二点才回家,曾老师不让他进家门。刘老师苦苦哀求也不行。
大冬天的,齁冷齁冷,已出落得人高马大的儿子急了开始砸门。曾老师便报了警。
警察听说是父子俩闹别扭,劝了几句就想走人。可曾老师不干了:“我作为一个公民,报了警,你们竟不管不顾!这完全是渎职,我要向上级部门投诉你们。”
警察也只好动了真格,把儿子给拘了。
新闻圈里,当大家把这则“逸闻”当笑话传时,我动了怒:“这是编造。都是圈里人,嘴下留德好不好?!”
可是过了几天,已是深夜二三点钟,我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,听筒里传来了曾老师有气无力的声音:“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……记着给我报警。就说是我儿子把我掐死的……我脖子上的掐痕,就是证据……”
我披衣下床,愣了好长时间。
又过了几年,我调到杭州工作。有一天,曾老师竟找上了门。
这时,他已退休。可退休的他,风头比在职时还劲:抢他的媒体多了去了。他在几家报纸、网站兼职,开了专栏;还频频以嘉宾身份在电视上露面。
我请他到湖畔居喝茶。他打开随身的手提电脑,给我看他接受境外媒体访谈时的视频。这时的他,笑语朗朗,满满的自信。
“你儿子……”我很想知道母子俩的状况,可话到嘴边,又吞了回去。
就这么一句,前一秒钟还逸兴遄飞的他,突然呆住了,愣怔了半天,捉住我的手哇哇大哭起来。
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有几个人,还好奇地离开座位走了过来。他不管不顾依然哇哇痛哭,鼻涕流了老长老长。
我赶紧给他塞纸巾,他不接,哭得一声比一声响。我知道他的脾气,劝也没用。就任他哭。
足足过了十几分钟,他才止住哭:“我对不起……对不起儿子啊……”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,我闻知了噩耗:林林患了脑瘤,而且是恶性的。
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少年一幕幕的过往。心里堵得难受。
他把我的手攥得生疼:“我儿子得脑瘤,是不是因为我经常揪着他的头发……往墙上撞引起的?你不知道……林林小时候……多……多么聪明……记忆力比我还好……”
我紧着劝解:“曾老师,您多心了。撞击只会得外伤,不可能引起肿瘤。”
“你说的是真心话?” 他直直盯着我, 一连问了好几遍。
那天,他让我陪他到灵隐寺去。
在观音殿里,他跪下臃肿的身体颤巍巍向观世音菩萨像磕头。别人一般是磕三个,他一连磕了几十个。并向功德箱里捐了厚厚一沓钱。
见有穿灰色僧袍的香客给观音像前的长明灯添油,他对我说:“你去问问,我能不能添?花多少钱都行。”
九
那年年底,我回北京开年会,打曾老师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,便向他的同事打听他儿子的状况,想去医院看看。
“已经过世了。”曾老师的同事说。
那个同事还告诉我,在儿子弥留的最后阶段,曾老师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:他不让别人服侍,在儿子身边搭了一张小床,天天端屎端尿,帮儿子擦拭身子……
在京期间,我多次联系他,都没能联系上。回杭后,每隔一段时间,我便试着拨一次他的电话,始终没能拨通。
三年前的一天夜里,突然,他的电话打了进来,声音已经非常虚弱,且断断续续:“小王,我的癌症……已……已……到了晚期。我要走了……请替我照看一下老伴儿。经济上,我不操心……有存款,还有两套房子。可……可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……”
哽咽了半天,他接着说:“我要去……和儿子……团聚了……我再不打他了……绝不再打他了……如果有来生……让他打我……我给他当儿子都成……”
我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个头发微卷、英挺俊朗的少年。如果他活到现在的话,也该接近四十了吧?
可他,却永远停在了25岁的年龄!
劳罕:作家,现居北京。
特约编辑 蓦 凡
原载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2023年第8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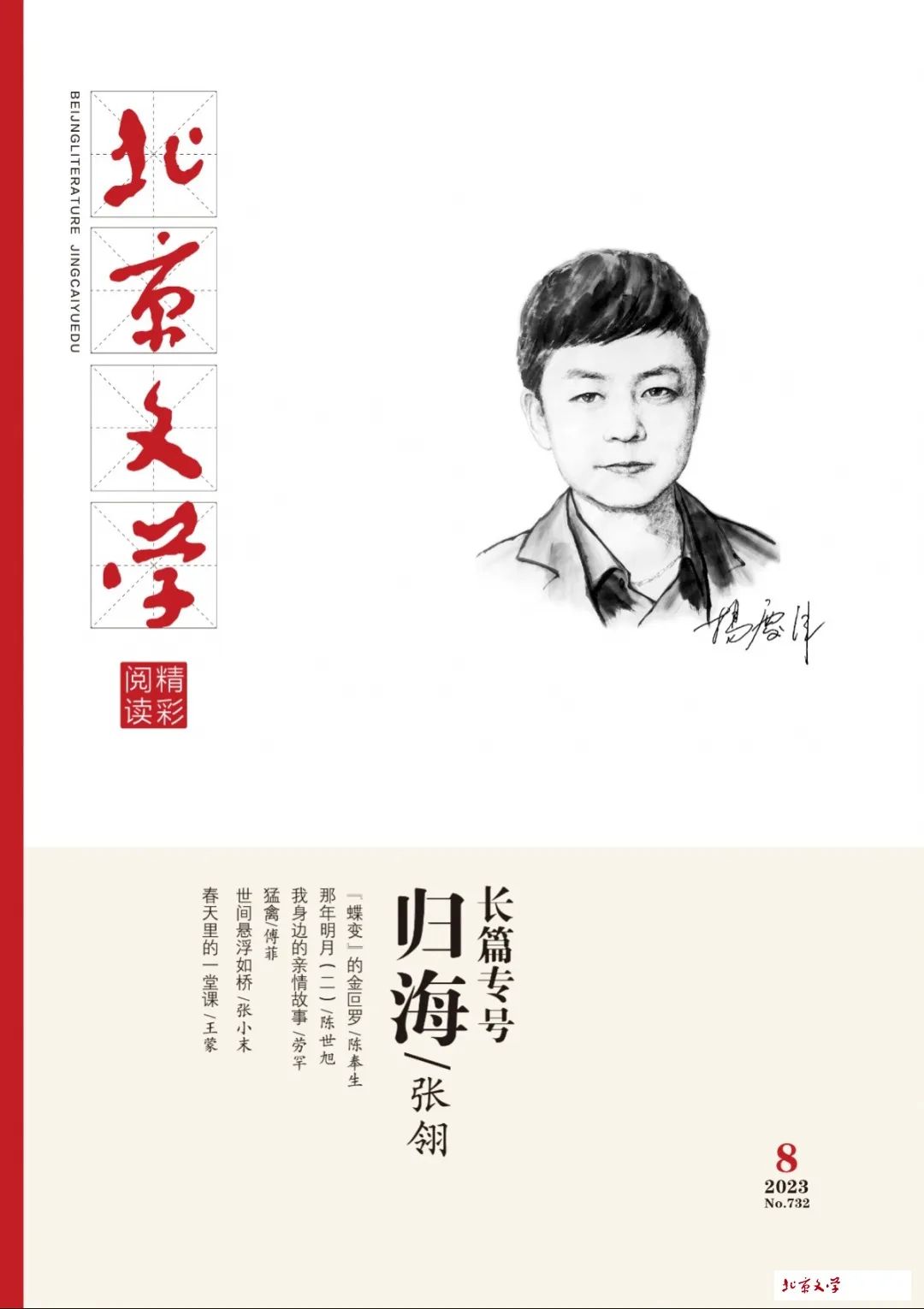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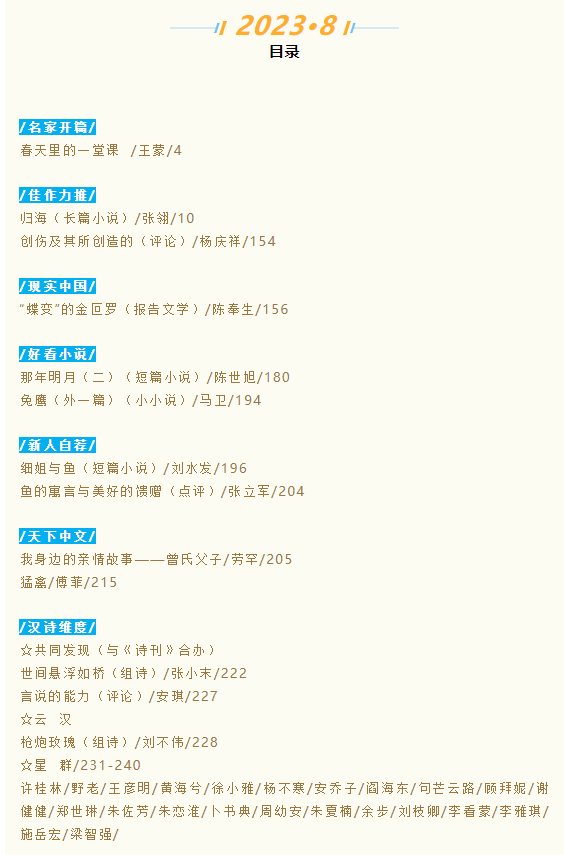




请输入验证码